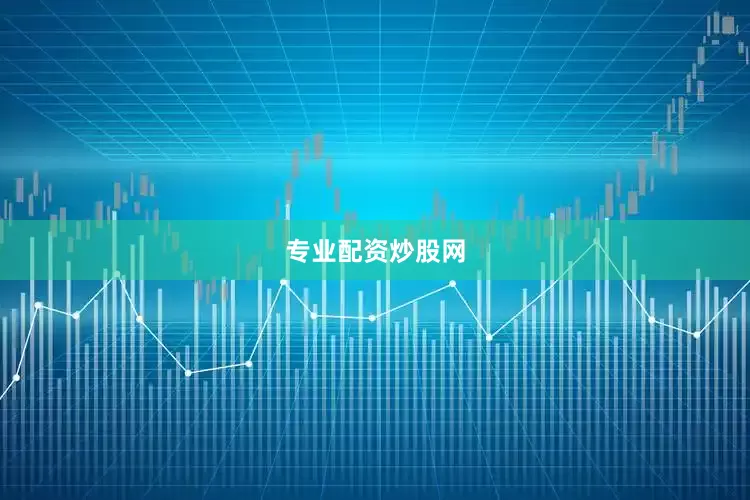《左传》对国家大事的总结非常简练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,意思是祭祀与战争,是国家最为重要的两项事务。这一观点最早并非针对周代社会,而是指殷商王朝。商朝对祭祀和军事的重视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,商朝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,终结于公元前1046年,前后存在约550年。然而,在这个存在了500多年的王朝中,几乎有四百年都在进行战争。
商汤通过“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”彻底推翻了夏朝,奠定了商朝的统治基础。在经历了约一百年的相对和平之后,商王仲丁在迁都于嚣(今郑州)后,商朝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征战,目标是周边的方国。仲丁征蓝夷,河亶甲征班方,武丁征伐鬼方、土方、羌方,武乙征犬戎,帝乙征伐夷方与盂,直到末代君主纣王在位时,商朝依然不断调兵遣将,东征西讨。
展开剩余81%相比之下,夏朝遗址如二里头遗址,出土的主要是祭祀用的礼器,偶尔会发现一些非实战性的兵器。而商朝则截然不同,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青铜器中,兵器的比例高达15%,而在殷墟晚期,出土的兵器比例更是上升到70%。尤其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中,竟有166座出土了实战兵器,且这些兵器出土的墓葬并不全是贵族墓,甚至平民墓中也有所发现。
殷墟的发掘不仅揭示了成批的青铜兵器,还出土了大量战俘的头骨,且这些头骨的种族多样,包括蒙古人种、太平洋黑人种、高加索白人种和爱斯基摩人种等。甲骨卜辞中明确记载,每当商王出征前,都会举行占卜和祭祀,而战争胜利后,又要向祖先进行祭祀,以表感谢。从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,商朝几乎是一个军事化的帝国,战争与祭祀几乎占据了商朝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。
那么,商朝为何如此热衷于战争?这不仅仅是因为殷人好战,背后可能有更加深层的原因。让我们先看看史书和甲骨卜辞中如何描述商朝的征战。仲丁征蓝夷,史书中写道“蓝夷作寇”,即蓝夷部落入侵了商朝的边境。武丁征伐土方、鬼方,记载称这些部落“数侵殷边侯田”,即它们频繁侵扰商朝的领土。商朝对羌方的征伐,卜辞中写到“贞乎吴御羌”,这说明是商王命令贵族吴去抵御羌族的入侵。至于商朝后期对东夷的征战,史书记载得非常清楚,“武乙衰敝,东夷浸盛,遂分迁淮、岱,渐居中土”,意味着随着武乙的去世,商朝的国力衰弱,东夷部落逐渐侵占中原。
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,商朝的对外战争大多可以归为两类:一是征伐背叛的诸侯和方国,二是对外来侵略者的自卫反击。考古研究也显示,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的时期,伊洛平原并未出现洪灾的迹象。即便在武丁时期遭遇洹水泛滥,商朝的都城安阳(殷墟)依然保持稳定,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迁都。
这也说明,商朝的五次迁都并非为了躲避洪水,而是与其军事行动的需要密切相关。例如,蓝夷侵扰,仲丁迁都至嚣,开始征讨蓝夷;班方作乱,河亶甲迁都至相;征伐东夷时,商朝迁都至殷(今安阳)。这些迁都的方向和征战的区域高度重合,显然反映了商朝在防御外敌的同时,战术部署与地理选择的密切关系。
但商朝周边的方国为何如此频繁地挑衅商朝呢?郭沫若曾提出,商朝的宿敌土方实际上是夏朝的遗民,他们在被商族击败后逃亡至西北,因此对商朝怀有深仇大恨。程憬学者也曾指出,夏民族的部分族人逃到西北,而另一部分则仍在东方,这解释了为什么商朝不断遭到来自夏遗民的入侵和挑衅。
这一学说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。根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,夏文化的遗址在汾涑盆地、长治盆地及环嵩山地区分布广泛,表明夏朝的文化延续在这些地区生根发芽。这些遗址的分布与商朝征战的方向高度一致,进一步证实了夏朝遗民及其后裔对商朝统治的反抗。
近年来,四川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新的证据。出土的陶器、玉器及牙璋等器物,显示了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。牙璋是夏文化的代表性物品,而三星堆出土的牙璋虽有所改良,但依然是祭祀用的重要器物。这一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商朝为何要远征蜀地的原因:夏朝灭亡后,部分夏遗民迁往成都平原,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。
综上所述,商朝虽然通过战争将自己从一个方国逐步扩展为中央集权的王国,但它的对外战争和统治秩序的维护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而商朝的周边,仍然充满了来自夏遗民及其支族的威胁,甚至连推翻商朝的周朝,其自称的“夏”国背景,也表明夏文化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。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十大正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系统2024年7月12日
- 下一篇:没有了